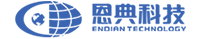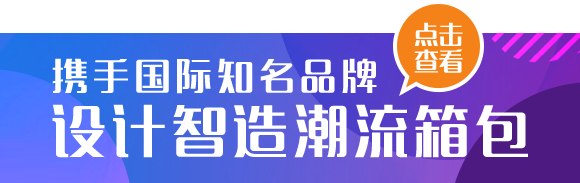惨白的光,从天花板上直射下来,刺得我睁不开眼。消毒水的味道,浓得化不开,钻进我的每一个毛孔。
我试着动了一下,左腿传来一阵钻心刺骨的剧痛,仿佛骨头被硬生生掰断,又用烧红的铁棍搅动着骨髓。
“别动!”一个护士的声音传来,带着一丝责备,“刚做完手术,腿不想要了?”
我转动眼球,看到了自己的腿。它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,外面是冰冷的金属支架,上面布满了螺丝和钢钉,像一个精密的刑具。
“三天三夜。”护士一边给我换药,一边说,“你小子命真大,子弹再偏一公分,你这条腿就废了。不过现在……也够呛。”
那是在西南边境,一片荒芜的戈壁。首长高振邦正在听取边防哨所的汇报,我像往常一样,站在他身后左侧三步远的位置,警惕地观察着四周。
我眼角的余光,瞥见远处山坡上的一点反光。那是狙击镜的反光!多年训练出的本能,让我来不及思考,甚至来不及喊出“卧倒”。
我昏迷前看到的最后画面,是首长那张棱角分明、波澜不惊的脸。他看着我,眼神里没有惊慌,没有关切,只有一种我读不懂的……深邃。
在我心里,高振邦不仅是首长,更是父亲,是偶像,是我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人。他军旅生涯战功赫赫,为人严厉,不苟言笑,却对我格外器重。他说我身上有他年轻时的影子,耿直,坚毅。
醒来后的第一天,来看我的人络绎不绝。我的老连长、营里的教导员、机关的干事……他们提着果篮,说着千篇一律的慰问话语。
我想象着他推开病房门的场景。他会像往常一样,背着手,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到我床前,用他那厚重的手掌拍拍我的肩膀,沉声说:“小徐,干得不错。”
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将我这个“英雄”,彻底遗忘在了这个充斥着消毒水味道的白色角落。
我又想,首长一定是被什么重要的事情绊住了。对,一定是这样。他是战区副司令,肩上扛着万千将士的安危,怎么能因为我一个警卫员,就耽误了军国大事。
可夜深人静的时候,当腿上的剧痛让我无法入睡时,那种被抛弃的冰冷感觉,就像毒蛇一样,噬咬着我的心。
他拿着我的X光片,指着上面那根刺眼的钢钉,告诉我:“徐锐,手术很成功,命保住了,腿也保住了。”
“但是,你的股骨粉碎性骨折,虽然用了最好的钢板固定,但神经和肌肉损伤是不可逆的。以后……你这条腿会留下永久性残疾,无法再进行高强度训练,甚至连快跑,都做不到了。”
其实,我早就知道了。每天晚上,当麻药的效力过去,那种从骨头缝里传来的、撕心裂肺的疼痛,就在告诉我这个事实。
我扔掉了轮椅,开始拄着拐杖,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练习走路。每一步,都像踩在刀尖上。汗水湿透了我的病号服,牙齿咬破了我的嘴唇。
我固执地认为,只要我能重新站起来,只要我能恢复得快一点,首长就会看到我的努力,他就会重新接纳我。
我甚至幻想着,他会给我安排一个文职岗位,让我能继续留在他身边,留在部队。
上面的红头和黑字,刺得我眼睛生疼。程序走得异常迅速,甚至能够说是迫不及t待。所有的手续,都已经替我办好了。
我没有说话,只是看着他,想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。但他很快就错开了目光,又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客套话,便匆匆离开了。
我这六年的青春,这半年的伤痛,这个我用一条腿换来的“英雄”称号,最终,只换来了这样一张纸。
我换上了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常服,这是我唯一舍不得扔的东西。我把所有的勋章、证书,都留在了病房的抽屉里。我不需要这么多东西来提醒我,我曾经多么愚蠢。
我背着一个简单的帆-布包,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衣物,和我母亲寄来的几双布鞋。
我站在马路对面,远远地望着。我看到一辆熟悉的黑色红旗轿车,从里面缓缓驶出。
车窗摇了下来,我看到了那张我日思夜想的脸。他坐在后座,正在看一份文件,神情专注而威严。
我看到他身边的副驾驶上,坐着一个新的、年轻的警卫员。那个年轻人,身姿挺拔,眼神锐利,就像……就像半年前的我。
我站在那里,直到那辆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,直到腿上的刺痛将我从麻木中唤醒。
南来北往的人群,操着各种口音,汇聚在这里,又奔向各自的目的地。空气中弥漫着方便面、汗水和廉价香烟混合的复杂气味。
我穿着那身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旧军装,背着沉重的行囊,一瘸一拐地在人群中穿行。每一次落脚,左腿的骨头都像被针扎一样疼。
我终于在候车厅的角落里,找到了一个空着的铁皮座椅。我坐下来,把拐杖靠在身边,将沉重的帆布包放在脚下。
我看着周围喧闹的人群。提着大包小包的民工,带着孩子回乡的年轻夫妇,满脸疲惫的出差白领……他们每个人脸上,都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,或喜或悲,或平淡或激昂。
我就像一个被从机器上拧下来的、生了锈的零件,被随意地丢弃在了一个陌生的角落,不清楚自己该去向何方。
回家的火车票,就揣在我的上衣口袋里。那是一张绿皮火车的硬座票,要坐三十多个小时。
我想象着回到家的场景。我年迈的父母,看到我这副样子,会是怎样的心痛。村里的乡亲,会怎样在背后议论我这个“瘸腿”的兵。
我抬起头,是一个约摸七八岁的小男孩。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运动服,脸蛋脏兮兮的,一双眼睛却又黑又亮。
他没有回答,而是飞快地伸出手,将一个被手心汗水浸得有些湿润的纸团,塞进了我的手里。

然后,他头也不回地转身,挤进拥挤的人群,一溜烟地跑了。我甚至来不及反应,他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不见。
那个孩子的眼神,我看得分明。那是一种被反复叮嘱过的、超越了他年龄的紧张和严肃。
我的心脏,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。在部队六年,我早已养成了超乎常人的警觉。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,这件事不简单。
我猛地站起身,环顾四周,试图寻找可疑的人。那个孩子的同伙,一定就在这附近!
但候车大厅里人山人海,每一张脸都是那么普通,又都显得那么可疑。我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,却找不到任何线索。
回家,意味着我年迈父母的期盼,意味着可以结束这噩梦般的半年,回到熟悉的环境。但也可能,意味着踏入一个早已为我准备好的陷阱。
不回,意味着踏上一条完全未知的、可能充满危险的道路。我不知道下一站会遇到谁,更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。
我攥紧了纸条,调整了一下背上的行囊,拿起拐杖,随着人流,走上了那趟不知开往何方的火车。
车厢里拥挤不堪,空气中混杂着各种难闻的气味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,把帆布包塞在座位底下。
我假装疲惫地闭上眼睛,靠在冰凉的车窗上,实则通过窗户玻璃的反射,警惕地观察着车厢里的每一个人。
我现在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孤狼,闯入了一片陌生的丛林。周围的每一个人,都可能是猎人。
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,带着一个哭闹不止的孩子。他们手忙脚乱地哄着,满脸疲惫。
过道上来回走动的,是卖着零食饮料的乘务员,和一些找不到座位、只能站着的旅客。
纸条上说“下一站”,却没有说具体是哪一站。这可能是对方为避免纸条被截获,也可能是一种试探,试探我是否会按照指示去做。
我拿出车票,上面印着这趟车的沿途停靠站点。一个小小的县城名字,映入我的眼帘——安平县。
这是从我上车的城市出发后,第一个停靠的站点,也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地方。
接下来的几个小时,我如同在执行一次最严峻的潜伏任务。我没有喝一口水,没有吃一点东西,将所有的注意力,都集中在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上。
我站在站台上,有些茫然。接下来该做什么?接应的人在哪里?他会用什么方式和我联系?
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,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,皮肤黝黑,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。他的手指关节粗大,布满了老茧。
他摇下车窗,没有看我,只是目视前方,对着空气,用一种毫无感情的语调说了一句:
这句话,是我还在老部队时,我们连队内部一句不起眼的紧急联络口令!知道这句话的人,不超过十个!而且,他们都是我最信任的战友!
“坐稳了。”司机吐掉嘴里的烟头,猛地一踩油门,车子像一头野兽,冲进了夜色之中。
一路上,我们没说一句话。车里的气氛,压抑得让人窒息。我几次想开口问他,到底是谁派他来的,但看到他那张刀削斧凿般、毫无表情的侧脸,我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车子没有开往县城中心,而是七拐八绕,驶进了一片破旧的居民区。这里的路灯昏暗,楼房也都是几十年前的筒子楼。
这是一个空置的房间,家徒四壁,只有一张光秃秃的木板床,和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。
“今晚你就在这里。”老马从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,拿出一部款式老旧的老人机、一沓用报纸包着的现金,还有几件看起来像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衣服。
“等等!”我终于忍不住开口,“你到底是谁?是谁派你来的?是高……是首长吗?”
我脱下了那身陪伴了我六年的军装,小心翼翼地叠好,放在了床头。然后换上了那身满是褶皱的旧衣服。
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苍白、眼神迷茫、穿着不合身衣服的“瘸子”,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陌生。
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,但我知道,从我换上这身衣服开始,我就已经踏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。

时间在这里仿佛失去了意义,白天和黑夜的界限,变得模糊。我能感知的,只有窗外光线的变化,和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心跳。
我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,焦躁,不安。我无数次地走到窗前,想拉开那厚重的窗帘,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但老马的警告,像一道无形的枷锁,束缚着我。
楼下是一个小小的院子,堆满了各种废品。有几个老人,天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,坐在院子里晒太阳,聊天。
这栋楼,是典型的八十年代建筑,出口不止一个。除了正门,后面应该还有一个通往垃圾场的后门。
我的房间在三楼,不高不低。如果发生意外,我可以从窗户跳下去,虽然会加重腿伤,但至少能保命。
我把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桌子,堵在了门后。又把那把摇摇晃晃的椅子,放在了窗边。
那两个人,穿着便装,但走路的姿态,和那种警惕的眼神,我一眼就能看出,他们是军人。
他们没有上楼,只是在楼下徘徊,假装在聊天,眼睛却不时地瞟向我所在的这栋楼,像是在确认着什么。
他叫孙平,是军区纠察部门的一个干部!我曾经在一次联合行动中,和他打过交道。
就在我心急如焚,不知所措的时候,桌上的那部老人机,突然发出了刺耳的震动声。
电话那头,是一个清冷的、不带任何感情的女人声音。她说完,就直接挂断了电话。
我抓起床头叠好的军装,塞进帆布包,背在身上。然后拿起拐杖,用最快的速度,冲出了房门。
我没有走楼梯,而是直接来到了楼道尽头的窗户。这里对着大楼的背面,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。
左腿传来一阵剧痛,但我顾不上了。我摔在柔软的垃圾堆上,巨大的冲击力让我一阵头晕眼花。
幸运的是,巷子口真的停着一辆橙色的环卫车。车门开着,一个穿着环卫工服的人,正在冲我招手。
我瘫坐在充满酸臭味的垃圾桶之间,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腿上的剧痛和死里逃生的后怕,让我浑身都在发抖。
她大约三十岁左右,穿着一身干练的黑色风衣,短发,眼神锐利而冰冷。她手里夹着一根女士香烟,红色的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。
“自我介绍一下。”她吐出一个烟圈,“我叫秦筝,地方国安部门的工作人员。”
“我们一直在秘密调查一条涉及军区高层的走私线。”秦筝看着我,眼神像X光一样,似乎能看穿我的一切,“而你,徐锐,是我们这次调查的关键。”
“那不是一次偶然的袭击。”秦筝的话,像一块巨石,砸进了我的心里,“那是境外间谍组织,针对高振邦的一次刺杀行动。而你,作为现场唯一的目击者和幸存者,已经被敌人盯上了。”
“高振邦为保护你,不让你成为敌人的下一个目标,所以才故意疏远你,用最快的速度让你伤残退伍,目的是让你脱离敌人的视线,从明处,转入暗处。”
“那个给你纸条的孩子,是我们安排的。老马,也是我们的人。这一切,都是高振邦在暗中委托我们做的。”
那座在我心中已经崩塌的偶像,在这一刻,又重新屹立了起来,甚至比以前更加高大,更加伟岸。
“他不好。”她说,“敌人很狡猾,内部渗透得很深。他现在处境也很危险,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。”
“现在,我们应该你的帮助。”秦筝说,“我们的调查陷入僵局,需要一个突破口。我们应该你回忆起事发当天,从离开营地到中枪前,所有你认为‘不正常’的细节,无论多小。”
我开始拼命地回忆。那天的每一个画面,都像电影一样,在我脑海里一帧帧闪过。
“我们原定的视察路线,是东线。”我说,“但是出发前一个小时,突然接到了命令,改走南线。这个命令,是赵副司令传达的。”
“还有,我们的车队里,有一部电台突然失灵了,导致我们和后方的联系中断了将近半个小时。”
“在经过一个叫‘狼牙口’的地方时,我看到路边有一个牧羊人,他的眼神很奇怪,不像普通的牧民,一直盯着我们的车队看。”
秦筝静静地听着,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,不时地做着记录。她的表情,始终像冰一样,没有一点变化。
“有……有一个。”我的声音有些不确定,“就在枪响的前一秒,我扑向首长的时候,我的余光……好像瞥见了跟在首长身后的赵副司令。”
“对。”我点了点头,“我记得很清楚,当时所有人都被枪声惊呆了,下意识地卧倒或者寻找掩体。只有他,赵景山,非常冷静地站在原地,脸上没有一点惊慌的表情。”
我一边说,一边模仿着当时看到的那个动作。我伸出右手,用拇指和食指的指肚,轻轻地、快速地捻动了一下,就像是在捻掉一粒根本不存在的灰尘。
“我当时情况紧急,没有多想,以为那只是一个人在极度紧张下的无意识小动作。”
她只是死死地盯着我模仿的那个手势,脸上的血色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一点点褪去。
她夹着香烟的手指,开始微微颤抖。一截长长的烟灰,掉落在她的黑色风衣上,她却浑然不觉。

她看着我的眼睛,那眼神里,充满了让我不寒而栗的东西——震惊,恐惧,以及一种……一种我没办法理解的,浓重的怜悯。
“徐锐,你记错了。这不是捻灰尘的手势。在我们的情报系统里,这个手势只有一个意思——‘清除次要目标,行动继续’。”
我猛地想到了什么,脸色煞白地看着秦筝。如果首长是主要目标,那……次要目标会是谁?
秦筝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,她缓缓地点了点头,那动作像是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。
“没错,那个‘次要目标’,就是你。赵景山有问题,他早就想除掉你了。那天,那颗子弹,根本不是射向高振邦的。”
我回想起这半年来的种种不公和冷遇,回想起高振邦那张冷漠的脸,回想起部队那快得不正常的处理程序……
“那…那首长呢?”我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声音因为激动而剧烈颤抖,“首长知道这件事吗?他让我退伍,是为保护我,对不对?是为了让我脱离赵景山的视线!”
她又从口袋里,摸出了一支烟,点上,深深地吸了一口,似乎需要尼古丁来给她勇气,说出那个最残忍的真相。
秦筝的每一个字,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冰刀,狠狠地扎进我的心脏,将我那可笑的信仰,搅得粉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