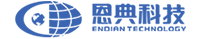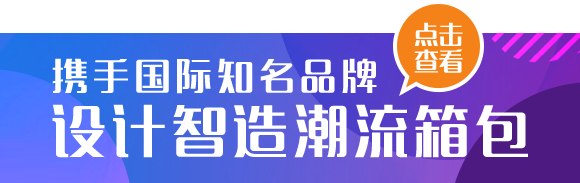1947年12月14日深夜,上海江湾一带的冬风啜泣,零下二度。简直所有人都在缩脖取暖时,战犯中野久勇摸出牢房,踩着院中残雪翻墙而去——这是上海战犯拘留所开办近一年里最离谱的一次戒备事端。后续追捕、暗查、再被捕,总共耗时七十六天,毕竟在1948年2月28日收场。整件事看似古怪,其实透着晚期监狱办理的懈怠,也反映出战后上海都市肌理中“侨胞、警探、小贩”这三股人流交错的共同现象。
中野是从“特高课”走出的老牌宪兵,三十七岁赴崇明,年仅三十五岁时已在岛上言出法随。战役完毕后,他被当地大众告发拘捕,1947年头押进江湾战犯拘留所。其时担任看守的,是由国防部直接分配的宪兵中队,却没想到十个月后让对方钻了空子。夜里灯光暗淡,巡查班排认为电网安定,巡视距离拖到半小时,值夜官更把钥匙挂在办公室内壁,全无防范。中野借上厕所之名出了门,推开半掩的行政房,拿了假造狱警证件,又顺着最矮处墙脚一跃而下。等清晨交代,点号时少了一人,看守才如梦初醒。

他外逃第一站是南京路。卖掉原本价值不菲的西装,换成灰色长衫;再到租界旧货铺淘得一顶破毡帽,生生把一个前宪兵改装成落魄生意人。几句僵硬的沪语,加上一口广东口音一般话,竟然骗过不少茶馆店员。有意思的是,这套假装的创意,来自他在崇明审问地下党员时的“反串试验”。当年他曾让部下假扮搬运工混进集市,现在轮到自己上场,算是恶有恶报中的一段挖苦。
二十余天里,他白日混迹北火车站,夜里躺在候车室长凳。钱不够了,就跑到乍浦路桥帮人力车推坡收“桥头费”。人群喧闹,警探排查困难,他反而相对安全。偏偏一次一般伤风改变了进程。为了退烧,他在药店买了散装阿司匹林,被装进纸包随身藏着。1月13日,他决议离沪去嘉定投靠旧相识,途经昆山。在嘉定南门,守城警员例行搜寻,翻开布包见粉末,心里一惊:“这怕不是白面?”所以把他扣下。没有身份证件,只要一张半新的华商存根,一看更可疑。所以嘉定警察局以“流窜贩毒”将其收押。
吊诡的是,中野被当地公安拘押、移送、复审前后四十六天,竟没人认出他是通缉战犯。原因有二:其一,当地卷宗体系里没有录入战犯相片;其二,短短半年内上海换过三次币制,一般警员忙着敷衍物价飞涨,搜捕情报底子跟不上。中野在法庭上后来满意地回想,“过三关而无人识”,说的便是这段阅历。
1948年2月21日,嘉定当地法院毕竟确定“粉末系阿司匹林”,将其无罪开释。正是这张释票,使上海警探判别战犯极或许又回来市区。由此,暗线全面收束到乍浦路桥一带。理由简略:越狱者身无分文,最易在桥头找零工。警方组织便衣迂回打听,成心雇人推车,再与之闲谈,辨口音、听行线日午后,桥堍上一个自称“王寿章”的推车汉抢生意,谈价时说出一句:“大饼现已要三千块啦!”“大”字拖音奇怪,一旁的暗探当即心头警铃高文:这人显着中文里带日式喉音。几秒之后,两名便衣一起攥住他的手腕,枪口顶住后腰,小声正告:“别乱动,跟我走。”

验指纹、比对旧档案,一张泛黄通缉照与面前人相叠,身份尘埃落定。当夜,提篮桥监狱把他收入重刑区,并当即陈述上海军事法庭。比较江湾,提篮桥的警得多:双层铁门、探照灯、装备放哨,还装备其时罕见的电台监控。中野再无时机翻墙,仅有的要求竟是“加餐五张大饼”,恰似还在想念那句露出身份的口误,令人哭笑不得。
4月1日,上海军事法庭公开审理。检控方递上崇明受害者家族证词、宪兵队内部备忘录、被害者遗体相片等十一份依据,指出他在1940年7月“崇明大屠杀”中直接命令射杀及沉江超越二百人。陪审席上一度万籁俱寂。法官石美瑜发问:“是否供认指挥了沉江举动?”中野先辩称受上司指令,后又说是部下擅自为之,前后说词对立。当检方播映当年宪兵队庆功酒会相片,上面他正碰杯笑谈“扔石头看浪花”,中野脸色铁青,低头不语。
4月8日上午九时,军法处核准死刑。押赴刑场途中,他与同案的上司大庭早志竟用日语合唱《君之代》。押送宪兵没有阻挠,只把安全扣全翻开,防范最终拼命。枪声在十分钟后响起,两名行刑战士各补一枪,承认不再呼吸。崇明受害者代表远远看着,没有放鞭炮,也无人喝彩,仅仅带着木然的神态连续脱离。他们更介意的是,不会再有人把亲人绑了石头扔进江里。

回到案子中心,中野久勇之所以能溜出江湾,一半归因于战后办理机制的缝隙:战犯未一致囚服,看守人员待遇偏低,电网保护不良;另一半则是都市流动人口的巨大保护伞。推车、当短期工、睡车站,简直与一般难民无异。若非那句“大饼三千块”,他或许真能混船返日。但前史总有细小的转折点,言语细节就成了定音锤。关于当年担任侦缉的警探而言,破案不是荷枪实弹的追逐,而是捕捉一句拖长的腔调。
这场越狱闹剧在档案中被归为“1948年上海战犯再捕案”,完毕时悄然无声。可关于崇明老大众来说,正义虽迟,毕竟未缺席。这一结局让人不由想到那句老话——法网难逃,疏而不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