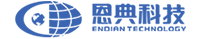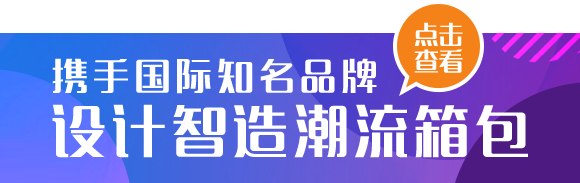铁锹碰到了一个硬物,我用力一撬,一个锈迹斑斑的车把从黑色的淤泥里露了出来。
二叔丢掉手里的锄头,脸色瞬间变得惨白,嘴唇哆嗦着,像是看到了什么极端恐惧的东西。
我没听他的,反而愈加用力地整理着周围的淤泥。很快,一辆简直烂成骨架的自行车露出了全貌。
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,在自行车的车筐里,我看到了一个早已腐烂不胜,但含糊能辨认出红格子图画的布包。

说话的是我二叔,周大海。他赤着脚站在没过脚踝的泥水里,古铜色的皮肤在太阳下泛着油光,手里那把锄头,使得虎虎生风。
我叫周军,本年三十五岁。刚从打工的南边城市,回到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——周家村。
我不是不想在外面混,实在是混不下去了。在工地上干了十几年,钱没攒下多少,反倒落下了一身缺点。前阵子扭伤了腰,老板二话不说就把我辞了。灰心丧气之下,我拾掇了行李,回了老家。
我爸爸妈妈走得早,是二叔二婶把我拉扯大的。二叔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,靠着几亩薄田和村后那个抛弃了多年的鱼塘过活。
我这次回来,二叔最快乐。他揣摩着,把那口荒了快二十年的鱼塘从头整理出来,养点鱼,咱们叔侄俩,也算有个营生。
二叔也没谦让,一坐在塘边的田埂上,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,点上一根,眯着眼睛看着我。
“仍是年青好啊,有劲。”他吸了一口烟,渐渐吐出个烟圈,“小军,这次回来,就别走了。在外面漂着,毕竟不是个事儿。咱叔侄俩,把这鱼塘搞起来,不敢说大富大贵,吃喝不愁是没问题的。”
看着二叔那张被年月刻满皱纹的脸,我心里不是味道。二叔这辈子,过得太苦了。
我的二婶,叫刘翠兰,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佳人。她不是咱们村的,据说是二叔年青时去镇上赶集,对她一见钟情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娶回家的。
二婶人长得美丽,心也巧,会做衣服,烧的菜也好吃。我小时分,最喜欢跟在她后边,她总是会变戏法似的,从口袋里掏出糖块给我。
我到现在还记住那天晚上。二叔和二婶由于一点小事吵了起来,吵得很凶。二婶哭着拾掇了几件衣服,装在一个红格子的布包里,推开门就冲进了雨里。
第二天,二叔报了警。差人来了,在村里村外找了好几天,一允许绪都没有。有人说,看到她往镇上的方向去了。也有人说,她或许回娘家了。可二叔去她娘家找,那儿的人说她底子没回去。
也有人说得更刺耳,说她本来就不是个本分的人,指不定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
二叔听了这些话,也不辩解,仅仅一个人喝闷酒,喝醉了就对着二婶的相片哭。从那以后,他像是变了个人,本来开畅的性情,变得默不做声,脾气也浮躁了许多。
这十五年,他一个人,既当爹又当妈地把我拉扯大,再也没提过续弦的事。村里人都说,他心里,还惦记着那个没良心的女性。
这口鱼塘,便是二婶失踪后,渐渐旷费的。曾经,二叔二婶会一同在这里养鱼、喂鸭,是他们爱情的见证。二婶走后,二叔再也没心思打理,任由它长满了荒草,成了一汪死水。
现在,咱们叔侄俩,要亲手把它整理出来,似乎也是想把那些不胜的曩昔,一同从泥里挖出来,晒个洁净。
塘里的水早就抽干了,剩余厚厚一层黑色的淤泥,又黏又臭。我和二叔干了整整三天,才整理出了一小半。
“歇会儿吧,小军。”二叔直起腰,用那条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汗,“我去村头小卖部买两瓶汽水。”
二叔走后,我看着眼前这片狼藉的鱼塘,心里揣摩着,得想个办法加快进度。这淤泥太厚了,光靠人力挖,不知道要挖到驴年马月。
我想到村西头的王瘸子。他家有台小型的柴油抽水机,曾经是用来抽水灌溉的,不知道能不能用来抽这些半干不湿的淤泥。
说干就干。我跟王瘸子联系还不错,小时分没少吃他家的梨。我跑到他家,跟他一说,王瘸子很爽快地就容许了。
“那玩意儿好久没用了,也不知道还好欠好使。你自己去柴房拉吧,用完了给我送回来就行。”
我千恩万谢,拉着那台布满尘埃的抽水机回了鱼塘。耍弄了半响,总算让它“突突突”地从头发动了起来。
我把粗大的抽水管伸进淤泥里,机器一响,黑色的泥浆就被源源不断地抽了上来,排到周围的水沟里。功率比咱们用锄头挖,快了十倍不止。
有了机器帮助,咱们干劲更足了。一下午的时刻,整个鱼塘底部的淤泥,就被整理得七七八八。一些板结得凶猛的当地,再用锄头和铁锹略微平坦一下就行了。
“估量是管子被啥东西堵住了。”我走曩昔,关掉机器,然后吃力地把深陷在淤泥里的抽水管往外拔。
洗着洗着,我感觉不对劲。这东西,摸上去硬硬的,还有些扎手。等上面的淤泥被冲掉,我才看清,那竟然是一截白森森的骨头!

二叔一把抢曩昔,辗转反侧地看,越看脸色越丑陋。他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,猪骨头、牛骨头见过不少,但一看这骨头的形状和巨细,他就知道,这必定不是什么牲口的。
二叔二话不说,拿起铁锹就冲了曩昔,对着那片淤泥张狂地发掘起来。我也赶忙拿起锄头跟了上去。
咱们俩愈加卖力地整理着周围的淤泥。很快,一个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车把,从黑泥里露了出来。
我其时还没反响过来,持续往下挖。自行车的概括越来越明晰,最终,整个车架都暴露了出来。是一辆旧式的二八大杠女士自行车,这种车子,现在早就看不见了。
他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泥地里,死死地盯着那个布包,浑身剧烈地哆嗦起来,嗓子里宣布“嗬嗬”的动静,像是被啥东西扼住了咽喉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来的是镇派出所的刘所长,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,皮肤乌黑,目光锋利。他一看便是个老刑警。
村子里的人传闻鱼塘里挖出了东西,也都纷繁跑来看热闹,把鱼塘围得风雨不透。
刘所长拉起了警戒线,把看热闹的乡民都隔在了外面。他带着两个年青的差人,穿上雨靴,亲身下到了鱼塘里。
他们对现场进行了细心的勘测。那辆自行车,那个布包,都被小心谨慎地取了出来,装进了证物袋。
“是……是我老婆的。”二叔的声响沙哑得凶猛,他蹲在田埂上,抱着头,整个人像是瞬间老了十岁。
“你老婆?周大海,你老婆不是十五年前就跟人跑了吗?”刘所长明显对当年的案件有形象。
刘所长又拿起那个装着布包的证物袋,看了看,然后转向我:“你说,你认得这个包?”
我点了允许:“我二婶走的那天晚上,背的便是这个包。红格子的,我记住清清楚楚。”
很快,更多的警车吼叫而来。差人们开端对整个鱼塘,进行地毯式的查找和发掘。
“周大海,你把你老婆失踪那天晚上的状况,再仔细心细地跟我说一遍!一个细节都不能漏!”刘所长亲身详细询问二叔。
“那天……那天晚上,咱们吵架了。”他时断时续地说,“就为了一点小事……我说她做的菜咸了,她就跟我顶嘴……咱们越吵越凶……我……我还着手推了她一下……”
“她就哭了,说这日子无法过了,然后就拾掇东西要走……我其时也在气头上,就吼她,说她走了就别回来……然后……然后她就冲出去了……”
二叔摇了摇头:“没有。那天雨下得很大,她便是背着那个包,跑出去的。车子……车子一向在宅院里放着。”
二叔茫然地摇头:“我不知道……她走后第二天,我发现车子不见了,我还认为……我还认为是她回来,悄悄骑走的……”
假如二婶走的时分没骑车,那她的自行车,为何会和她的包一同,沉在鱼塘底下?

差人把当年和二叔二婶有过触摸的人,简直都问了一遍。但十五年曩昔了,很多人的回忆都现已含糊,供给不了什么有价值的头绪。
我被叫进去问话的时分,把自己理解的状况都说了。我说二叔尽管脾气欠好,但很疼二婶,不或许做出损伤她的事。我还提到了当年村里那个谣言,说二婶跟一个城里的卡车司机联系不一般。
屋子里,静得可怕。墙上,还挂着二婶那张现已泛黄的黑白相片。相片上的她,笑得那么甜,那么美。
“小军,”二叔忽然开口,声响沙哑,“你说……你二婶她……是不是真的现已……”
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,只能拍了拍他的膀子:“二叔,别瞎想,差人会查清楚的。”
“大海哥,小军。”他把东西放在桌上,脸上带着一丝巴结的笑,“我传闻出了这事,过来看看你们。”
我和二叔都有些意外。王瘸子这人,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小气和不合群,平常很少跟人交游。今日怎样会自动上门?
“大海哥,你也别太难受了。这事……都曩昔这么多年了。”他干巴巴地安慰着。
“没……没事。”王瘸子急速摆手,“便是……便是来看看。那什么,我传闻,差人在问十五年前的事?”
王瘸子缄默沉静了一瞬间,像是下了很大的决计,忽然凑了过来,压低了声响说:“大海哥,有件事,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当年……当年弟妹出事那晚,我……我如同看到点东西……”
“我……我也记不清了……就……便是那天晚上,雨下得很大,我起夜上厕所,如同……如同看到一个人影,鬼头鬼脑地在你家鱼塘那儿晃悠……”
“天太黑,雨又大,看不清脸。”王瘸子摇着头,“就觉得那人个子不高,有点……有点跛脚……”
这个刘三,是村里有名的无赖,游手好闲,游手好闲,还由于偷东西,瘸了一条腿。当年,他就没少打扰过年青美丽的二婶。二叔还由于这事,跟他打过一架。
二婶失踪后,这个刘三也在村里消失了一段时刻,说是出去打工了。过了几年才回来,比曾经更落魄了。
“千真万确!”王瘸子拍着胸脯,“我便是怕惹麻烦,才一向没敢说。今日看差人都来了,我深思着,这事可不能再瞒着了。”

他家大门紧闭,街坊说,从今日下午差人来到村里开端,就再也没见过他的人影。
整个周家村,都被一种严重又压抑的气氛笼罩着。所有人都觉得,只需抓到刘三,十五年前的谜案,就能真相大白。
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集在追捕刘三身上时,一个更让人意想不到的状况,发生了。
第二天一早,市里派来的法医和技术人员,对那辆自行车和布包,以及那截指骨,进行了开始的判定。
刘所长指着陈述上的一行字,对我说道:“法医对那截指骨进行了判定。成果出来了。”
刘所长的目光,变得史无前例的锋利,他死死地盯着我,渐渐说出了一句让我如坠冰窟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