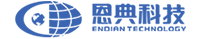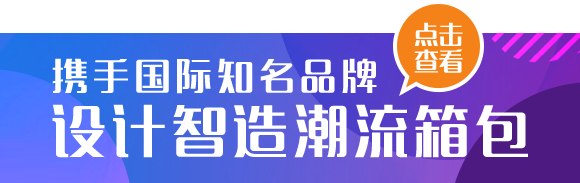金陵郊外的山桃花,本年开得分外刺眼。一簇簇的,没个规矩,挤满了山坡,白里透着不健康的粉,像哭肿了的眼。
官道被三千铁骑踏得烟尘蔽日。马蹄声沉得发闷,敲在人心上似的。最前头那人,一身玄色常服,腰杆挺得垂直,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。只要那双眼睛,黑沉沉的,望着前头山路拐弯处。
“陛下,前头便是青云观了。”锦衣卫指挥使周德兴催马接近半个身位,动静压得很低。
朱元璋没应声,仅仅勒住了缰绳。马打了个响鼻,不安地践踏着地上。他抬手,死后滚滚的铁流便忽然停下,只余下马匹粗重的喘息和盔甲冲突的细响。
一座小庙的概括从山沟里显露来。灰扑扑的墙,黑黢黢的瓦,半掩在几棵老柏树后边。庙门前的石阶陡得很,缝里钻出乱草,两扇木门色彩脱落,在风里晃悠,宣布吱呀——吱呀——的动静,听得人牙酸。
朱元璋眯了眯眼。三十年了。那个当地,那股疼,还有那张严寒的脸,非但没含糊,反而像生了根,在骨头缝里时不时刺一下。成了皇帝,四海归心,万民生杀,可有些夜里,他仍是会梦见自己从高高的台阶上滚下来,浑身骨头像散了架,嗓子里满是泥腥味和血味。
“回陛下,查得清楚,便是青云观。住持法号无尘,本年该有八十了,一向没离开过。”周德兴答得妥当。
朱元璋点点头,翻身下马。动作有些沉。周德兴赶忙也跟着下来,朝后头使了个眼色。精骑无声地散开,刀出半鞘,弓弦微张,将这破庙围得铁桶一般,连只鸟都甭想飞出去。
门板撞在里边的墙上,又弹回来少许。一股子陈年的香火味混着尘埃气,扑面而来。
庙堂很小,光线暗淡。正中的佛像金漆斑斓,垂着眼,似看非看。供桌上的香炉倒了,香灰洒了一片。一个老僧背对着门,坐在一个蒲团上,佝偻着身子,手里渐渐捻着一串磨得发亮的念珠,嘴皮子轻轻动着。
一张干燥得像老树皮的脸,皱纹深得能夹住东西。眼睛污浊,眼皮耷拉着,可目光落在朱元璋身上时,却让朱元璋心头莫名地一紧。那目光太安静了,像一口枯井,扔块石头下去,都听不见响。
“知道。”无尘点点头,动作缓慢,“从你坐上龙椅那天起,贫僧就知道,你早晚会来。”
朱元璋脸上的那点表情消失了,只剩余一片冷硬。“好。你记住就好。”他往前走了两步,靴子踩在积尘的地上上,留下明晰的印子。“三十年前,也是在这儿,朕在你庙门口,跪了半宿,求一口吃的。你记住你怎样对朕的?”
“你开门,看了朕一眼。”朱元璋的动静不高,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,“朕求你,抱住你的腿。你抬脚就踹在朕心口!”他手指着门外那峻峭的石阶,“朕就从那儿,一路滚下去!九十九级!浑身没一块好肉!”
“那时分朕就想,要是能活下来,有朝一日,非回来扒了你的皮!”朱元璋盯着无尘,“今日,朕来了。”
“重八。”无尘又明晰地重复了一遍,“这一个姓名,你没忘吧?骨头烧成灰,也该记住。”
“活?”无尘摇摇头,污浊的眼睛望向门外那片被兵刃映亮的天空,“八十岁,够本了。仅仅临了,有件东西,得还给你。”
他哆哆嗦嗦地伸手,探进那件洗得发白、打着补丁的僧袍怀里,摸了半响,掏出一个布包。布是灰色的,脏得看不出本性。他一层层,极端缓慢地揭开。
粗瓷的,灰黄色,碗口缺了不规则的一大块,边际良莠不齐,像是摔碎的。碗身上有好几道裂纹,最深的一道简直贯穿碗底。任谁看了,都会觉得这是该扔进垃圾堆的褴褛。
可朱元璋看到这半个碗的瞬间,脸上的血色“唰”地褪了下去。他猛地往前踉跄一步,死死盯住那破碗,嘴唇抿成一条惨白的线,胸口剧烈地崎岖起来。
周德兴从未在皇帝脸上看到过这种表情。那不是愤恨,更像是一种猝不及防的震动,乃至……有一丝惊慌?
“眼熟?”无尘把碗托在干瘦的掌心,往前送了送,“重八,这碗要是还在,你敢杀我?”
四个字,像四根严寒的钉子,把朱元璋钉在了原地。庙外三千甲士,庙内孤身老僧,输赢存亡本该一点点没有悬念。可这半个破碗一呈现,局势遽然变得怪异起来。

日头毒辣辣地挂在天上,把地皮烤出一指宽的裂口,像一张张渴死的嘴。河沟早就见了底,剩余板结的、灰白色的泥块。井水打上来,又浑又涩,咽下去刮嗓子。
爹朱五四躺在土炕靠里的方位,只剩余一把骨头架子,被子盖在身上都看不出崎岖。他嗓子里宣布“嗬嗬”的动静,眼睛直勾勾望着漏光的房顶。
娘陈氏坐在炕沿,拿着块破布,一遍遍给爹擦脑门底子不存在的汗。她的眼眶深陷,颧骨挺拔,脸上是一种麻痹的灰败。
朱重八蹲在门口的门槛上,看着外面白花花的日头。他十六了,个子却没窜起来,瘦得像根插在地上的竹竿,衣服空荡荡地挂着。肚子里火烧火燎地疼,那不是饿,是空了太久,肠胃拧在一同的钝痛。
陈氏颤巍巍地从怀里摸出半个黑乎乎的东西,递过来。是半个糠菜团子,硬得能砸死人,不知藏了多久,边际都发黑了。
“傻话……”陈氏的眼泪滚下来,在灰扑扑的脸上冲出两道痕,“吃了,才有力气……”
终究,那个团子谁也没吃。三天后,朱五四死了。死之前,他枯柴相同的手死死攥侧重八的手腕,攥得生疼,嘴唇翕动了好半响,才挤出几个气音:“活……活下……去……”
朱重八没哭作声,眼泪顺着脏兮兮的脸颊往下淌,和汗水混在一同。他和娘用家里最终一张破席子,裹了爹,在村后山坡挖了个浅坑埋了。土刚填平,娘就一头栽倒在坟头边。
他跪在爹娘那个简直看不出痕迹的土堆前,磕了三个头。脑门抵着滚烫的地上时,他咬着牙,从牙缝里挤出动静:“爹,娘,儿子必定活下去。必定。”
他离开了村子,沿着被太阳晒得发软的土路,漫无目的地走。路上偶然能看到倒毙的人,蜷缩着,很快就被苍蝇围满。一开始他还怕,后来就麻痹了。
遇上心软的人家,能得半碗淡薄的菜粥,或许一块硬饼子。八成时分,迎候他的是紧锁的门扉,不耐烦的呵责,乃至追打出来的棍棒。
他睡过旷费的土地庙,蜷在供桌底下。也钻过人家堆柴火的草垛,被虫子咬得浑身是包。最饿的时分,他蹲在路旁边,看着一滩半干的牛粪,里边有几粒没消化完的豆子。他盯着看了好久,久到眼睛发花,最终伸出手,把豆子抠出来,在衣襟上蹭了蹭,塞进了嘴里。豆子很硬,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他囫囵咽下去,胃里一阵抽搐。
就这么走,走了不知道多久。鞋底早就磨穿了,脚上磨出血泡,血泡破了结成厚茧。衣服破成一条一条,牵强遮体。
这天黄昏,他走到一座山脚下。昂首看,山顶模糊有座庙的影子。有庙,就有和尚。和尚,总该有口吃的吧?
石阶又陡又长,如同永久爬不完。他爬几步,就要歇好一阵,眼前阵阵发黑。汗水流进眼睛里,刺痛。但他不敢停,那点弱小的期望拽着他,一步步往上挪。
总算,他爬到了庙门口。两扇褪色的木门紧锁着,上方一块旧匾额,写着“青云观”三个字。
期望一点点灭下去,剩余的是更深的失望和虚脱。他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,背靠着严寒的木头。算了,就这样吧。死在这儿,清净。
一个和尚站在门内。不高不矮,三十上下的年岁,面庞冷硬,没什么表情。他手里拿着一把半旧的扫帚,看着瘫坐在门槛外的朱重八,眉头轻轻蹙起。
朱重八像是快要淹死的人看到了木头,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,猛地扑曩昔,一把抱住了和尚的腿。
“师父!救命!给口吃的吧!我两天没吃没喝了!快不行了!求求您!发发好心!”
和尚的腿绷紧了。他垂头,看着脚下这个衣冠楚楚、浑身污秽的少年,目光里没有怜惜,只要一种深不见底的安静,或许说,冷漠。
“师父!求您了!就一口!一口粥就行!”朱重八抱得更紧,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
朱重八“啊”地一声惨叫,整个人向后飞跌出去。天旋地转,后背、臂膀、腿,连续磕在坚固严寒的石阶棱角上,疼得他眼前发黑,连喊都喊不出来了。他像个破麻袋,不受操控地一路滚落,“砰砰”的撞击声闷响着,一向滚到最下面的平地,才停住。
他瘫在泥地里,浑身上下无处不痛,骨头像是全碎了。嘴里一股腥甜,他咳了几声,吐出一口带着血丝的唾沫。
他吃力地抬起头,望向高高的石阶顶端。那个和尚还站在庙门口,高高在上地看着他,身影在暮色里像个冷漠的剪影。
一股混杂着疼痛、耻辱和张狂的恨意,猛地冲上头顶。他竭尽全身力气,沙哑地朝着上面吼:
“秃驴!你记取!我朱重八!今日要是死不了!将来!必定回来!拆了你这破庙!扒了你的皮!”
庙门口的和尚,仍旧没什么反响。就在朱重八认为他会回身进去,或许再下来补上一脚的时分,和尚却回身,消失在了门内。
是一个粗瓷碗,灰黄色,和他见过的全部碗没什么不同,乃至更旧些,碗口还有个小小的缺口。
朱重八躺在那里,脑子里乱糟糟的。踢他下去,又给他扔吃的?这和尚是疯子吗?
可肚子里的疼痛和生计的天性压倒了全部。他伸出手,抓过那半个硬馒头,拼命往嘴里塞。馒头又干又硬,碎渣呛得他直咳嗽,但他仍是饥不择食地,三两下就吞了下去。肚子里有了点真实东西,那火烧火燎的感觉略微停息了些。
他又抓起那个碗。碗很粗糙,边际的釉磕掉了几块,摸着喇手。他把碗紧紧攥在手里,冰凉的触感让他清醒了一点。
他挣扎着,用那半个馒头积储起的一点点力气,摇摇晃晃地站起来。浑身的骨头都在反对。他朝着庙门的方向,渐渐地,鞠了一躬。
他用这个碗,讨过稀粥,接过残羹,也喝过路旁边的脏水。碗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,是他“活下去”最真实的依托。
后来,他漂泊到皇觉寺,被收留当了和尚。庙里日子也贫苦,但好歹有口安稳饭吃。他识了字,念了经,也学着看人脸色。那个破碗,被他用块旧布细心包好,放在枕头底下。
灾荒年景,寺里也断粮了。和尚们被派出去“化缘”。朱重八又捧着这个碗,走上了老路。他走过更多的当地,见过更多的惨状,也受过更多的冷眼和欺辱。碗沿上的缺口,如同又多了两个。
有一次,在山路上赶夜路,他脚下一滑,摔了个狠的。怀里的布包摔出来,里边的碗“咣当”一声磕在石头上。他匆忙捡起来,就着月光一看,心里咯噔一下。
朱重八坐在地上,捧着两片碎碗,发了半响呆。最终,他捡起大的那片,擦了擦。小的那片,他看了又看,终究是用布从头包好,塞进了怀里。大的那片,他持续用来吃饭喝水。裂了的碗边简单割嘴,他就当心地转着圈喝。
再后来,全国越来越乱。他扔了僧袍,投了红巾军,跟着郭子兴交兵。刀头舔血,危在旦夕。但他怀里,一直揣着那小半片碎碗。没人知道为啥,他自己有时也忘了它的存在,只要偶然换洗衣服摸到,才会愣一下神。
南征,北战。身边的人死了又来,来了又死。他从朱重八,变成了朱元璋,又从一个小兵,成了元帅,成了吴王。实力渐渐的变大,地盘越来越广。
登基前夜,应天府的新皇宫里,灯火通明。朱元璋独自坐在没有彻底安顿好的书房里,面前摊着舆图,心里却空落落的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,触到那个硬硬的布包。
他把它拿出来,在灯下翻开。那小半片碗,在亮堂的烛火下显得更为破旧不堪,裂缝的边际泛着陈年的污渍。
朱元璋把布包推曩昔:“把这个,收到内库最里头去。找个保险的箱子装好,不许任何人碰,也不许任何人知道。”
李德海双手接过,下手沉甸甸、硬邦邦的。他不由得悄然用手指捏了捏,感觉是片瓷器?心里疑惑,皇上登基在即,什么瑰宝没有,怎样要藏这么个破东西?但他脸上不敢显露分毫,恭顺应道:“是,奴婢遵旨。”
马皇后点点头,一眼瞥见他手里捧着的布包,边际显露一点灰黄色粗瓷。“李公公,这拿的是什么?”
“重八,”马皇后走近,口气温文,“我听李德海说,你让他收了个旧物件?是什么宝物,大典前还要特意安顿?”
朱元璋身子几不行察地僵了一下,头也没回:“不是什么宝物,曾经用过的一个破碗,藏着没用,扔了又……算了,收起来省心。”
“看什么看?”朱元璋忽然转过头,口气有些冲,“一个破碗有什么美观的!朕说收起来就收起来!”
马皇后怔住了。夫妻多年,朱元璋对她历来尊敬有加,很少用这样不耐烦乃至带点肝火的口吻说话。她没再坚持,但心里却画了个问号。那个破碗,绝不寻常。
朱元璋盯着无尘手里那半个碗,又看看刚刚从宫中快马取来、放在香案上的别的半个。两个半碗的断口狰狞地对着,像是在无声地叫嚣。
“这碗,本便是庙里的。”无尘慢慢道,“三十年前,你拿走了大的那片。小的这片,你丢在山路上了。贫僧捡了回来。”
“破碗?”无尘抬起眼皮,看了他一眼,“对你来说,它或许是个破碗。对贫僧来说,它是件该还的东西。”
朱元璋不再说话。他走近香案,拿起宫中取来的那半个碗。这是他了解的那片,大的那片。碗底的裂纹,碗沿的磕痕,乃至当年他用来喝粥时,嘴唇常触摸的那一小块当地,好像都被磨得略微润滑些。他用手摩挲着,冰凉的粗粝感透过指尖传来。
一声极轻的闷响。不是严丝合缝,究竟摔碎多年,边际有些细微的崩缺。但大体上,它们拼成了一个完好的、布满裂纹的碗的形状。
朱元璋捧着这个拼合起来的碗,重量好像比幻想中沉。他下意识地翻转碗身,看向碗底。
碗底粗糙,积着经年的尘垢。但在接近中心的方位,有几道划痕。不是烧制时的痕迹,更像是后来用尖利的东西,一下一下刻上去的。
由于尘垢,之前独自看半个碗时,底子不会留意。现在拼合,尘垢在刻痕处略有不同,那笔迹便模糊显现出来。
看清后朱元璋像是被一道无形的响雷击中,整个人猛地向后一晃,手里的破碗差点脱手。
他死死捉住碗,指关节捏得发白,眼睛瞪得滚圆,死死盯着碗底那几个字,又猛地昂首看向无尘。
“不……不行能……”他的动静抖得不成姿态,“你……你是谁?!这字……这字是谁刻的?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