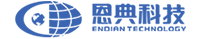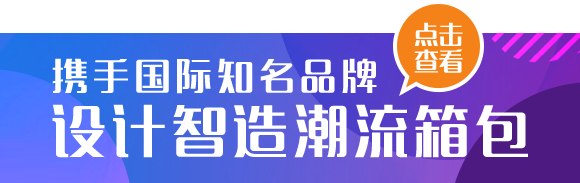“林海啊,不是嫂子说你,你这眼光是不是被猪油蒙了?那苏家大姐二姐,哪个不是村里一枝花?你偏偏选了那个……那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老三?你这是娶媳妇仍是娶个闷葫芦回家啊?”
“结壮能当饭吃?你也不看看苏家那老太婆的脸,黑得跟锅底似的。你这哪里是娶亲,几乎是替她们家整理库存!今后有你懊悔的时分!”
林海拍了拍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二八大杠,迎着冬风,脸上挂着傻笑。他怀里揣着一张刚办妥的结婚证,红得棘手,红得耀眼。
冬风卷着雪花,把苏家庄的土路冻得梆硬。林海穿戴一件袖口磨破了边的旧棉袄,兜里揣着向工友借来的两百块钱,跟在媒妁王婶死后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苏家走。

大姐苏玉梅,在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,那是多少人仰慕的铁饭碗。她烫着时尚的浪,穿戴红呢子大衣,走路带风,眼睛历来不看脚底下的泥地。
二姐苏玉竹,是县纺织厂的一把手,长得文静秀气,说话细声细语,传闻厂里的技能员都在追她。
只需老三苏玉兰,是个没人疼的草窝里的凤凰。她从小发烧烧坏了喉咙,说话吞吞吐吐,性情又内向,整天不是在灶台边散步,便是在猪圈里忙活。在这个家里,她就像个透明人。
“到了,便是这家。”王婶推开苏家的大门,扯着喉咙喊,“春花嫂子!人带来了!”
苏母王春花正坐在堂屋里嗑瓜子,眼皮子都没抬一下,仅仅鼻孔里哼了一声:“进来吧。”
堂屋里生着火炉,暖洋洋的。大姐苏玉梅正对着镜子涂口红,二姐苏玉竹在织毛衣,两人看了林海一眼,目光里都透着一股不加粉饰的厌弃。
“这便是那个下岗工人?”苏玉梅撇撇嘴,“穿得跟个土包子似的,还想娶我?做梦呢吧。”
“姐,你少说两句。”苏玉竹尽管也不满意,但还算谦让,“人家毕竟是来相亲的。”
苏母吐掉瓜子皮,斜眼看着林海:“林海是吧?传闻你刚从厂里下岗?家里还有个患病的老娘?我可丑话说在前头,我家大梅和二竹,那但是皇亲国戚,彩礼少了一千块免谈。别的,还得在县城有套房。”
林海苦笑了一下。在这个人均薪酬只需两三百的时代,这几乎是狮子大开口。他摸了摸兜里那两百块钱,觉得棘手。
“婶子,我……我现在没那么多钱。但我有一把子力气,我会开车,我能跑运送赚钱。只需您肯把闺女嫁给我,我确保今后让她过上好日子。”林海诚实地说。
“好日子?画大饼谁不会啊?”苏母翻了个白眼,“没钱就别想癞蛤蟆吃天鹅肉。逛逛走,别耽搁咱们家闺女找好人家。”
紧接着,一个穿戴打补丁的蓝布罩衣的姑娘,端着一碗热火朝天的鸡蛋面走了出来。她低着头,不敢看人,仅仅默默地把面放在林海面前的桌子上。
那是一双清澈见底的眼睛,像山涧里的泉流,洁净得让人心颤。尽管她脸上蹭了一点烟灰,头发也有些杂乱,但那种朴素和仁慈,却像冬日里的暖阳,瞬间照亮了林海暗淡的心。
苏玉兰点了允许,脸红到了耳根,那是她特意给这个“不幸人”做的。她知道母亲和姐姐们看不上他,怕他饿肚子。
“好吃。”林海大口吃了一口,面条筋道,荷包蛋煎得金黄流油,那是他吃过最好吃的面。
“传闻了吗?老林家那小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?放着供销社的售货员不要,非要娶那个哑巴老三!”
“这就叫王八看绿豆,对上眼了呗!估量是感觉自己穷,配不上人家金凤凰,只能找个草鸡将就过日子。”
苏母尽管觉得林海脑子有病,但转念一想,老三在这个家里便是个赔钱货,并且由于口吃一向嫁不出去,现在有人乐意接盘,还能收点彩礼(尽管林海只给了两百块,外加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当聘礼),几乎是天上掉馅饼的功德。
“行行行!你要领走就领走!今后过欠好可别退货!”苏母生怕林海反悔,连像样的陪嫁品都没给,只给了苏玉兰两床旧被子和一个珐琅脸盆,就把人打发了。
苏玉兰尽管话不多,但四肢极端利索。她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,寒酸的窗户被她糊上了新纸,还剪了红双喜贴上;冷硬的土炕被她烧得暖洋洋的;就连林海那件破棉袄,也被她补缀得整整齐齐。

为了省钱,他舍不得住旅馆,就在驾驭室里窝一宿;舍不得下馆子,就啃干馒头喝凉水。
但每次出门前,苏玉兰都会早上两个小时,给他烙好一摞带着葱花和猪油的大饼,煮好十几个咸鸭蛋,装在洁净的布袋里。
“路……路上……慢……慢点。”她总是站在村口,目送着林海的车消失在尘土中,直到看不见停止。
林海每次回来,不管多晚,家里总是亮着灯,桌上总是扣着热饭。苏玉兰会端来一盆热水,蹲在地上给他洗那双满是机油和臭汗的脚,然后用针挑破他脚底的水泡。
“不……不苦。”苏玉兰笑着摇头,给他递上一杯泡了枸杞和红枣的热水,“甜……甜着呢。”
推开门,暗淡的火油灯下,苏玉兰正坐在炕沿上,手里拿着针线,正在补缀一副寒酸的手套。那是林海修车时用的,早就磨穿了,他正计划扔了买新的。
“玉兰,这个给你。等咱们攒够了钱,我就把这破房子翻盖了,让你住上大瓦房。”
苏玉兰接过头巾,爱不释手地摸了又摸,眼圈红了。她拉着林海的手,神秘兮兮地把他拽到床边。
苏玉兰掀开枕头,小心谨慎地拆开枕芯的一角,从里边掏出了一个裹得结结实实的蓝布包。
林海以为是媳妇平常节衣缩食攒下来的几块钱买菜钱,笑着说:“你留着花,我不缺钱。”
当最终一层布被揭开,借着火油灯弱小而跳动的亮光,林海看清里边的东西时,整个人如遭雷击,浑身的血液在这一会儿似乎欢腾了,直冲天灵盖!
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缺、普通人一个月薪酬才两三百的时代,这三千块,几乎便是一笔巨款!是一笔能压死人的巨款!
“这……这哪来的?”林海吓得说话都结巴了,“玉兰,你……你不会是去抢银行了吧?”
更让他震动的是,钱中心夹着一张发黄的信纸。上面画着杂乱的草药图谱,灵芝、天麻、何首乌……周围还有一行歪歪扭扭、像小学生写的字:
“这是我上山采药、悄悄在后山种香菇、木耳攒的。俺不傻,俺仅仅嘴拙。拿着,换个新车胎,把车修好,安全回家。你在,家就在。”
苏玉兰从小跟着村里的老赤脚医生跑山,认得几百种草药。她知道哪片山坡长野山参,哪个树根底下有灵芝。
结婚前,她在娘家不受待见,采来的药材、种的香菇都悄悄藏在后山的一个山洞里,攒够了就背到远处的收买站去卖。她不敢把钱拿回家,由于一旦被苏母知道,必定会被搜刮得一尘不染去补助大姐二姐。
“玉兰,你真是我的女诸葛啊!”林海擦干眼泪,看着眼前这个衰弱却坚韧的女性,眼里满是敬仰和爱意。
有了这三千块钱的启动资金,林海不只给卡车换了四条簇新的轮胎,大修了发动机,还剩下不少钱。
苏玉兰也不再藏着掖着了。她使用自己的草药常识和种饲养技能,开端在自家宅院里和后山大规模栽培香菇和木耳。

她开端在村里收买其他乡民采摘的土特产,分类、暴晒、包装,然后让林海顺路带到城里的农贸市场去卖。
夫妻俩配合默契,一个主内收买加工,一个主外运送出售。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,没过两年,林海就成了村里第一个盖起两层小洋楼的人,还买了彩电、冰箱。
大姐苏玉梅嫁给了镇上的一个所谓“大款”,成果那人是个赌鬼,把家产输了个精光,还经常打老婆。苏玉梅整天哭哭啼啼回娘家借钱。
二姐苏玉竹嫁给了厂里的技能员,原本挺好,成果赶上了下岗潮。技能员下岗后心里不平衡,酗酒成性,苏玉竹为了养家,不得不去摆地摊卖袜子,风吹日晒,早没了当年的水灵。
她怎样也没想到,当年那个被她作为“赠品”甩出去的哑巴闺女,居然成了金凤凰。
“老三啊,你看你现在兴旺了,也不能忘了娘家人啊!”苏母一进门,就往真皮沙发上一躺,那姿势像是太后回宫,“你大姐夫欠了赌债,你二姐夫没作业,你当妹妹的,得帮衬帮衬。拿个五万块钱出来,先给她们救救急。”
“妈,我……咱们的钱,也是……也是辛苦赚的。没……没那么多。”苏玉兰低着头,吞吞吐吐地说道。
“没那么多?你骗鬼呢!林海那大车天天跑,钱像流水相同进账!”大姐苏玉梅尖嘴薄舌地说道,“再说了,这生意你能做,还不都是靠咱妈把你养大?我看啊,这生意不如交给咱们娘家打理,你一个结巴,能管好什么账?别让人骗了!”
“便是,把账本交出来,让你二姐夫来管,他是文化人。”二姐苏玉竹也赞同道。

苏玉兰的身体在哆嗦。从小到大,她习惯了委曲求全,习惯了被剥削。但这一次,她看着这个十分困难建立起来的家,看着墙上她和林海的结婚照,一股从未有过的勇气从心底涌了上来。
苏玉兰猛地抬起头,尽管声响还在颤栗,但目光却反常坚决,“这……这是我和林海的家。我不……不欠你们的。彩礼……最初都给你们了。生意……是我做的,谁……谁也不给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