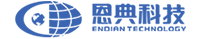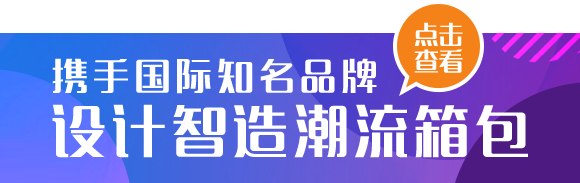1990年的夏天,热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我是李贵仁,二十九岁,棉纺厂的机修工。那天车间里闷得像蒸笼,机器轰鸣声混杂着热浪扑面而来,我刚钻在毛病织布机底下修完零件,满手油污地爬出来,额头上的汗混着油渍往下淌,就看见搭档小王嬉皮笑脸地朝我跑过来。
“贵仁哥,下班有事没?”小王凑到我跟前,声响压得低低的,眼里藏着狡黠,“我姐说要给你介绍目标,特别让我约你今晚见见。”

我愣了一下,擦汗的手停在半空,沾了一片黑印子:“你姐?”我跟小王的姐姐素未谋面,只听他提过在大街办上班,是个热心肠。
“可不是嘛!”小王拍了拍我的膀子,“我姐说厂里就你还单着,急得不可,非让我有必要把你约出来。定心,这次找的姑娘都靠谱,有个在百货公司布料货台上班,长得可清秀了!”
我垂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机油的蓝色工装,袖口磨得发毛,心里泛起一阵犹疑。这些年母亲没少催婚,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也像苍蝇似的围着转,相亲的次数两只手数得过来,却总由于种种原因不了了之。要么是对方嫌我作业油腻,要么是我觉得没眼缘,一朝一夕,我对相亲也没了多少等待。
“行吧,几点?在哪见?”纠结了半响,我仍是点了头。母亲的想念声在耳边回响,二十九岁的年岁,在当年的确算得上“大龄青年”了。
下班后我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往家赶,一路迎着热浪。到家后翻出衣柜里最面子的行头:洗得发白的白衬衫、灰色卡其布长裤,还有那双擦了三遍才牵强看不出污渍的黑皮鞋。镜子里的我普普通通,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,仅有能拿出手的,大约便是目光还算明亮,透着股真实劲儿。
相亲地址约在人民公园的凉亭,黄昏六点半,暑气稍退,公园里挤满了纳凉的人,摇着蒲扇的白叟、追逐打闹的孩子,还有成对漫步的情侣,热烈又惬意。我提早十分钟到的,刚走到凉亭邻近,就看见小王身边站着个穿碎花连衣裙的姑娘,扎着清新的马尾辫,落日洒在她脸上,衬得皮肤白皙,眼睛亮闪闪的。
我的心跳莫名快了几分,短促地走过去。没等我开口,姑娘先大方地笑了笑,声响像夏天的冷风,清清新爽:“你便是李贵仁吧?我是小王的姐姐,王雯雯。”
我红着脸点允许:“你好,我是李贵仁。”说话间,小王在一旁指手划脚,悄悄朝我使了个眼色,回身就溜:“姐,人我给你带到了,你们聊,我还有事前撤了!”
凉亭里瞬间只剩咱们两人,气氛一会儿变得奇妙起来。石凳被太阳晒得还藏着余温,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,手都不知道往哪放。仍是王雯雯先打破缄默沉静,指了指对面的石凳:“坐吧,别站着了,天还热着呢。”
我刚坐下,就看见她从蓝色手提包里掏出一叠相片,摊在膝盖上:“我先给你介绍下,这个是张梅,我搭档,在百货公司上班,人勤快心细,爸爸妈妈都是教师,知书达理的。”她拿起一张圆脸姑娘的相片,眼里满是真挚。
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,相片上的姑娘笑得腼腆,但我的目光却总不由得往她自己身上飘。落日的余晖落在她的睫毛上,投下细密的影子,她仔细介绍的姿态,比相片上的姑娘更让我心动。
“这个是刘丽,在邮电局作业,性情生动,会唱歌跳舞;还有我表妹,在纺织技校读书,下一年就结业,有文化...”王雯雯一张一张地介绍,语速轻柔,时不时昂首看我的反响。
“都挺好的,便是...总觉得差点什么。”我厚道答复,话一出口就有点懊悔,怕伤了她的善意。
王雯雯愣了一下,随即笑出了声,眼睛弯成了月牙:“你眼光还挺高呀!那这个呢?人民医院的护理,温顺又仔细。”她又拿出一张相片。
“护理太忙了,我怕今后顾不上家。”我摇了摇头。她连续介绍了五六个姑娘,我都没允许,王雯雯的热心逐渐变成了困惑,最终收起相片,带着点斗气的口气说:“李贵仁,这么多好姑娘你都看不上,你究竟想找什么样的?”
我被问得语塞,脸一会儿热到了耳根。其实不是姑娘们欠好,仅仅我心里装着眼前这个人,那些相片再美观,也抵不上她一笑的容貌。就在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时,王雯雯忽然歪着头,半恶作剧地说:“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?”
空气瞬间凝结了。蝉鸣声忽然变得分外嘹亮,我的心“咚咚”直跳,像要跳出嗓子眼。王雯雯说完也意识到不当,脸腾地红了,匆忙摆手:“我恶作剧的,你别当真!天不早了,我先回去了!”
王雯雯的脚步顿住了,逐渐转过身,眼睛瞪得大大的,满是惊奇:“你说什么?”
话已出口,我干脆豁了出去,深吸一口气,仔细地看着她:“王雯雯,我说实话,你比相片上的全部姑娘都好。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,我就觉得特别舒畅。你这么热心肠为我介绍目标,能这么为他人考虑的人,一定是个仁慈的好姑娘。我知道这很冒失,但我是仔细的。”
她呆住了,张了张嘴没说出话,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,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手提包的带子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悄悄叹了口气,从头坐回石凳上:“李贵仁,你可真怪。”
“我知道,所以我不求你现在就容许,就想求你给我一个寻求你的时机。”我严重得手心满是汗,等着她的答复。
夏夜的和风吹过凉亭,带来一丝凉快。王雯雯缄默沉静了顷刻,看着公园里逐渐亮起的路灯,忽然笑了:“那...就先共处看看吧。不过我可说好了,要是觉得不合适,咱们就到此为止,不许羁绊。”
那个晚上,咱们没再提相亲的事,绕着人民公园走了一圈又一圈,聊得满是家常。我知道了她在大街办担任档案收拾,喜爱看路遥的《普通的国际》,爱养猫,家里那只叫“花花”的橘猫特别黏人;她也听我讲修机器的趣事,比方某次为了抢修设备熬了通宵,最终被厂长表彰的事,听得前仰后合。
她想了想:“明日要加班收拾大街档案,后天晚上有场新上映的电影,我搭档暂时有事不去了,要不...你陪我去?”
“好!”我一口容许,看着她走进胡同深处的背影,站在原地久久没动。1990年的这个夏夜,我第一次觉得,这座生活了二十九年的小城,本来这么温暖。
咱们的“共处看看”,一晃就继续了三个月。那时候处目标,没有现在这么多把戏,无非是看电影、逛公园、下班送她回家。我会节衣缩食给她买水果糖,她会在我加班时送来热乎的饭菜;我记住她为了给我补衬衫纽扣,手指被针扎得冒血珠,她记住我爱吃青椒肉丝,每次碰头都特意做给我吃。
十月初的一个周末,王雯雯忽然说:“带我去你作业的车间看看吧,想知道你平常是怎样干活的。”
周日下午,我带她进了棉纺厂。车间里机器轰鸣,空气中飘着细微的棉絮,她却一点不厌弃,跟在我死后仔细地听我介绍织布机、纺纱机。走到一台我上星期刚修好的织布机前,她忽然指着机器缝隙说:“这儿如同夹着东西。”
我折腰一掏,是张折得整整齐齐的手艺贺卡,上面用彩色笔画着“生日快乐”,落款是“关怀你的工友们”。我愣住了,再过五天便是我三十岁生日,这些年母亲逝世后,我就没再过过生日。
“必定是小王他们悄悄放的,想给你惊喜。”王雯雯笑着说,眼里亮闪闪的,“三十岁是大生日,有必要过!我来组织。”
生日那天是周三,下班后我在厂门口等她。六点半,王雯雯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来了,车筐里放着个蓝布包。“上车,我带你去个当地。”她拍了拍后座。
“少烦琐,快上来!”她伪装气愤地瞪了我一眼。我只好小心谨慎地坐上去,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番笕香,心里暖暖的。
她把我带到了护城河边。秋天的黄昏很安静,柳枝随风摇摆,河水泛着粼粼波光。王雯雯从布包里拿出格子布铺在草地上,又掏出三个饭盒、两个苹果,还有一个小蛋糕——那时候蛋糕仍是稀罕物,上面插着三根细细的蜡烛。
饭盒里是她亲手做的菜:西红柿炒鸡蛋、青椒肉丝,还有满满一盒米饭。我拿起筷子,尝了一口青椒肉丝,咸淡刚好,是我爱吃的滋味。“你怎样知道我宠爱这一个?”
“前次一同去饭店,你就点了这个,吃了满满一大碗。”她随口说着,垂头帮我拨了块蛋糕。
我心里一热,本来这些不起眼的小事,她都记在心里。那天我许了个愿,希望能和眼前这个仔细温顺的姑娘一向走下去。吹灭蜡烛时,王雯雯忽然说:“其实一开端,我真便是单纯想帮我弟的搭档介绍目标,没想到把自己搭进去了。”
她摇摇头,眼里闪着光:“不懊悔。你尽管迟钝,不会说漂亮话,但你诚心对我好。前次我伤风发烧,你连夜敲开药店的门给我买药;下雨看电影,你把外套全披在我身上,自己淋得半湿...”
她一件件数着,我也跟着回想起那些细碎的温暖。暮色渐浓,我悄悄抓住了她的手,她没有躲开,手心暖暖的。1990年的秋天,我总算抓住了归于自己的美好。
冬季来得很快,咱们的爱情也逐渐变得深,开端商量着见两边家长。可就在十二月底,王雯雯忽然神色凝重地找到我:“贵仁,大街办有个去深圳的名额,领导引荐了我,至少要去两年。”
深圳,那个在其时只存在于新闻里的南边城市,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。我知道这是个好时机,可心里却像被什么堵住了,又酸又涩:“你...想去吗?”
那段时刻咱们都很缄默沉静。路过街上新开的婚纱照相馆,橱窗里的模特穿戴皎白的婚纱和笔挺的西装,咱们会不谋而合地停下脚步。“真美观。”她轻声说。“你穿必定更美观。”我仔细地说。
元旦那天,她给了我答案:“我决议去深圳,趁年青多学点东西。”动身日期定在一月底。接下来的日子,咱们恨不得把每一分钟都黏在一同,我带她见了我父亲,她也带我回了家,小王理解咱们在一同后,笑得直拍大腿:“我姐这媒妁当得,真是‘肥水不流外人田’!”
临行前夜,咱们在火车站邻近漫步,冬夜的北风吹得人颤栗。她忽然说:“贵仁,要不咱们算了吧,两年太长了,我不想耽搁你。”
“别胡说。”我把她的手紧紧攥在手里,哈了口热气暖着,“两年罢了,我等你。咱们咱们能够写信,也能够打电话,等你安稳了,我就去看你。”
送她上火车那天,站台上挤满了人。她靠窗坐着,我在窗外站着,四目相对,千言万语都堵在嗓子里。火车鸣笛时,她忽然翻开车窗,塞给我一个信封:“等我走了再看!”
火车慢慢发动,她用力挥手,我跟着跑了几步,直到火车变成一个小点。翻开信封,里边是一张合影——是咱们第一次在人民公园碰头时,她悄悄请路人拍的。相片反面是她清秀的笔迹:“李贵仁,等我回来,咱们就成婚。”我握着相片,又哭又笑,心里的信仰无比坚决。
1991年的异地恋,全赖函件维系。我每周写两封信,跟她讲厂里的事、父亲的身体;她回信虽慢,却会细细描绘深圳的高楼大厦、繁忙的作业,还有对我的怀念。夏天我请了十天假,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去看她,她瘦了些,却更精力了,眼里闪着我从未见过的光荣。她带我去看海,指着彼岸说:“那儿是香港,传闻今后会回归。”
她靠在我肩上,声响软软的:“想,特别想你,想家里的全部。再等我一年,我就请求调回去。”
1992年春天,她的调回请求批下来了,秋天就能回家。我快乐得一夜没睡,开端悄悄准备求婚。节衣缩食三个月,买了一枚小小的金戒指;托朋友找联系,在刚鼓起的商品房小区订了一套两居室,尽管要借款,但我想给她一个安稳的家。
九月,我去火车站接她。当她推着行李箱从人流中走出来时,我一眼就看见了她——剪短了头发,穿了件时尚的连衣裙,笑脸仍是那么了解。她跑过来扑进我怀里,周围的人来人往都成了布景。“我回来了。”她在我耳边说。“欢迎回家。”我紧紧抱着她,感觉全国际都圆满了。
我带她去看那套毛坯房,她兴奋地在空房间里转圈,规划着卧室放什么床,书房要做多大的书橱,厨房要摆哪些厨具。看着她叽叽喳喳的姿态,我从口袋里掏出戒指,单膝跪地——这个从电影里学来的新潮求婚方法,让她瞬间红了眼。
1993年五一劳动节,咱们成婚了。婚礼在棉纺厂的食堂办的,摆了十几桌,搭档亲朋都来了。她穿了件赤色旗袍,我穿了套新西装,在咱们的祝福声中,咱们敬了酒,成了夫妻。
婚后的日子,有甜美也有琐碎。她下班晚,我就提早回家煮饭;我加班,她就带着热饭菜去车间等我。1994年,咱们的女儿李思雯出生了,抱着软软的小丫头,我感觉自己是国际上最美好的人。
现在三十年过去了,女儿早已成家,我和雯雯也都退休了,还住在当年借款买的那套房子里,装饰了好几次,每一处都藏着咱们的回想。今日阳光很好,雯雯在阳台上浇花,我坐在沙发上看报纸。她忽然回头问:“你还记住1990年夏天,在人民公园第一次见我的姿态吗?”
“怎样不记住。”我放下报纸,走到她身边,抓住她的手,“你穿件碎花连衣裙,笑起来眼睛像月牙,一开口就把我魂儿勾走了。”
她笑了,眼角的皱纹堆在一同,像怒放的花:“那时候你傻呵呵的,一脑门子汗,还沾着油污,我心想这小伙子怎样这么真实。”
“好。”我点允许,紧紧握着她的手。阳光洒在咱们身上,温暖得像1990年那个夏夜的风。
韶光仓促,许多东西都变了,棉纺厂早已改制,人民公园翻修了好几次,可有些东西永久没变——比方我对她的爱,比方咱们相守终身的许诺,比方那个夏天,一句玩笑话牵出的一辈子温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