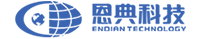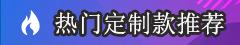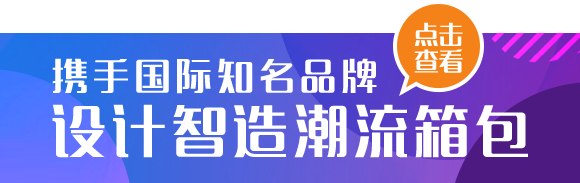将近午夜了,天还微微亮着。北极圈内的八月基本上没有一刻是彻底黑暗的。一点光透过红色薄纱窗帘在地毯上投下了暧昧的影子。我跪在床边,把最后一件毛衣卷成圆筒,填满背包里的最后一寸缝隙,然后用力拉上拉链。
这是我在挪威北部Lofoten群岛上的最后一个晚上。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,先乘大巴去群岛最北端,然后换乘著名的“北极圈列车”,一路前往斯德哥尔摩。
我在岛上住了一周,在一家青旅的女生宿舍,一座木质渔民小屋二层最靠南的房间。八月底已经过了挪威旅游的最旺季,这间有六个床位的宿舍今晚只住了我自己。
这不是一家普通的青旅,四十多年的历史让它积累了一批忠实粉丝,年复一年地不断返回。甚至曾在2002年的旅行专栏里,把它被誉为“世界上最好的青旅”。即使如此,这里并不广为人知。主人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,坚持不挂靠任何网络站点平台,只凭旅客之间口耳相传。要想预定必须按最传统的方式打电话,被主人用纸笔记录下信息。
我收拾完行李躺在床上发呆。时光在这里被拉长,不经意间就飘走了。许多人原本只打算停留三两晚,却一整周一整月地住了下去。我同他们一样不舍得离开,意犹未尽,仿佛马上要从一场好梦中醒来。
这么晚了,会是谁?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一个身影,却又马上抑制住这个念头,起身去开门。
近两米的男人弯着腰站在通向房间的梯子上。他的头发是金棕色的,微微卷曲,胡子留了有一段时间,理成一个随性的造型。虽然身高异常显眼,但并不健壮,反而给人感觉清冷。或许也是眼神的缘故。
他看向我。眼神比平往要温柔些。手里还举着一枝花。那是岛上随处可见的一种粉紫色野花,嫩绿色的根茎上还沾着露水,大概刚刚被摘下来。
我很惊讶。欣喜喜悦隐藏起来,时我暗中慌张。我不知该如何回应这突如其来的示好,只能侧身让他进到房间里。
岛上的公共交通不方便,我在雨里等了很久才坐上前往青旅的大巴,幸而只是蒙蒙的雨。这群岛本身就是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,而青旅所处的小镇更是角落中的角落。
群岛共有五部分所组成,全部在北极圈内,高纬度带来无常的天气和极端的生存环境,因此人烟稀少。虽然在维京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人类定居,但捕鱼业是唯一的经济活动,直到上世纪末旅游业的到来。游客们为了风景而来,大多只聚集在几个著名景区,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依旧冷清。青旅选址在这里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。
虽然早就听闻此地的传说,但真正身临其境却又是另一番感受。我推开门走进青旅的客厅。客厅里的人围成两圈。一头的人讲着意大利语聚在一起看地图,而另一头的人正传着吉他弹唱英文民谣。
我环视四周寻找可能是店主的人,最终撞上他的目光。他起身让我跟他走,说店主在另一栋房子里。
其实穿过门口的码头就到了,我们只说上几句话。我得知他叫Ignas,是立陶宛人,在拍一部关于这家青旅的纪录片,从二月开始住在这里。
那时我并未对他格外留意,甚至连他的长相都没有看清楚。唯有他的声音令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不紧不慢的透着慵懒的低沉声调和周围的环境很相配。
青旅建在码头上,出门就是北冰洋。还有两只小船供客人们免费使用,随时都可以借来木浆和鱼竿,划到海里钓鱼。我不会钓鱼却总能碰见会的人带我同去。
手划船去不了太远,所以钓上来的大部分是小型鱼,很适合烤来吃。我们在海边支起烤架,生起火,边吃鱼边交换天南地北的故事。
其中一天,店主格外有兴致,带上我和另几个客人去深海,开着他的专业渔船。船上有一块小屏幕连着雷达,能实时监测鱼的密度。在红点密集的位置放下钩子,很快就会有鱼上钩。
这片海域未经过度开发,资源保存得丰厚,店主一辈子都在海边生活,捕鱼经验是无人能及的。在他的指导下,我亲手钓上来一只半米长的海鲈鱼。其他人也都各有所获,有人也钓上来海鲈鱼,还有鳕鱼和野生三文鱼。
返程的时候,有经验的人慢慢的开始处理起鱼杂碎来,把内脏取出来,扔给附近观望的海鸥。这些白身黑翼黄喙的大鸟成群结队地追逐我们,此起彼伏地鸣叫,迎着太阳翩翩起舞。那是我从来就没见过的景象。
青旅的一面是海,另一面是山。不钓鱼的时候我就在爬山。这里的山很陡峭,最难的地方甚至要攀着铁索才能通过。因为陡峭所以人迹罕至,经常走上几个小时都见不到其他人的影,只有大片大片,看不到边际的绿色。窸窸窣窣的瀑布随处可见,走渴了可以每时每刻接上一瓶泉水来喝。还总有野生蘑菇和浆果出现在路边,可以采回去煮汤、熬果酱。
这些日子里我和Ignas的接触并不多。我每天都在认识新鲜的人,尝试新奇的体验,基本上没有一刻是空闲下来的。
而他比我更忙,拍摄记录片之余还要帮店主处理各种杂事。洗衣机漏水了,淋浴间排水口堵了,甚至运木柴的拖拉机坏了,都需要他来处理。除此之外还要时不时地接待客人,整理房间。
我对他的印象大多来自于晚餐。一到晚上总会有人在公用的厨房里,招呼大家一起做饭吃,他没事的话也会加入。我发现他的话不多,却总能点到关键处。经常来的老客人似乎都很信任他,甚至半开玩笑地推举他成为店主退休后的接班人。新来的客人也经常谈到他,有人没记住他的名字,就以“那个高个子的人”指代。
直到一天下午,我爬山回来的时候碰见他坐在在码头上晒太阳。“嘿,你饿不饿?我正打算去做鱼饼。”他突然对我说。“好啊。”对于食物我是来者不拒的。
我看着他拿来一块解冻的鱼肉,大概是谁钓来吃不完的,还有共享食物架上的一根胡萝卜、半头洋葱、几片圆白菜叶和一只鸡蛋,也是离开的客人留下的。他把鱼肉碾碎,把蔬菜切成丝,加入蛋液搅拌,然后在剪锅里摊成饼状。本来还应该加一点面粉,手头没有,就把面包撕成屑替代。他熟练地搭配这些被剩下来的食材,操作流畅自如,好像能把任何东西快速变成一道美味。而相比之下,我就拘谨得多,做饭的时候总要提前搜索菜谱,照着准备原料,然后一步一步跟着做。
做好鱼饼的时候还没到饭点,厨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,我们边吃边聊天。我给他讲故乡的北京,童年的纽约,现在居住的巴黎,和这些年旅行中的高光时刻。他也提起出生长大的城市,但更多还是讲述青旅的故事。
这间旅舍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创建的,本意是给季节性工作的渔夫提供落脚处,哪知收留的旅客慢慢的变多,逐渐演变成如今的青旅。店主以他的人格魅力营造出乌托邦一般的独特氛围。而这也吸引来一批独特的客人,参与进来,成为这氛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“愿意长途跋涉来到这偏僻又阴冷的地方,一定是些有意思的人。”Ignas是这么认为的。
“你在这儿住了这么久,当一切慢慢的变成了日常,还会感到特别吗?”我向他提出疑惑。
“为什么?”我有些惊讶,毕竟和这里的许多人相比,我绝对算不上经验比较丰富的旅行者。
采访并未能如期进行。第二天我们刚在客厅的桌子前架好摄像机,Ignas就接到了店主的电话,拖拉机又发动不起来了。青旅的热水要靠烧柴火加热,需要从附近的林子里砍柴,用拖拉机运回去。那台机器很老了,最近经常出故障,这次又坏在了半路。
“我本来想今天在这里开心一会儿,”他无奈地挂了电话,“但没办法,只能再找时间了。”
再次找到时间已经是我要离开的前一天。客厅里一直有别人,Ignas便提议到我住的房间拍摄,他还没在这里录制过采访。两个法国女生今天早上刚离开,这间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,后面两天也还没有人预定。
面对摄像机,我难免有些紧张。我是一点都没有化妆的,而且刚刚钓鱼回来,头发也被海风吹乱了。
我的心好像被什么拨动了一下,但马上又恢复原位。这些天来他一直表现得很专业,不像是会随便调情的人。除了青旅和纪录片,他很少和我讲起其他。而且在这里住的六个月,他什么样的女孩没见过呢?
说是采访,其实更像是聊天。他问我怎样得知这个青旅,为什么想来这里,实况和想象中是否相同......最终又讨论到旅行的意义。
“所以你为什么喜欢旅行?为何需要经历颠簸的路途而不是留在舒适的家中?”他从镜头后面问。
“也差不多,我喜欢与人相关的故事。这也是拍这部纪录片的目的,记录这里的人。”他回答。
我给他讲了我的故事。我做科研,正在读计算机博士,研究的是当下最热门的人工智能。我一路都在名校读理工科,日常接触到的人都极其相似。有人和我一样做计算机科研,有人在互联网大公司当程序员,还有人做量化金融或战略咨询。我们好像同一盘象棋里的子,只能按既定的规则前进,就算再跳脱也不过能走个“日”字。我努力想逃离这盘棋局,去看外面更广阔的世界,旅行是方式之一。
采访完毕,我们又一起做了晚饭,还是用鱼。我们做了一大锅鱼汤,分给所有人吃。这是我在青旅的最后一顿晚餐,我同每个人一一道别,热烈交谈。而他仿佛置身事外,话比往常还要更少些,不过似乎一直在看我。
晚饭后我又在过道里碰见他几次,每一次气氛都要更微妙上一分。我可以感觉到他穿过人群向我靠近,我明明心跳得厉害,却又要装作云淡风轻。
“都要半夜了,我一般不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做安排。”我回答,然后逃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我收拾完背包躺在床上发呆。我感觉我们之间会发生啥吧?但又能怎样呢?我明天一早就要离开,我们不过是彼此人生中最浅淡的过客。
他进到房间里,在窗户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。我也到他身旁坐下,把他给我的花放在面前的茶几上,盯着看。
别的房间里的人大概都睡了,除了风拍打玻璃的动静,听不见任何声响。我感到一股张力在寂静中蔓延,我好像该说些什么。
虽然是夏天,但北极圈里的夜总是冷的,而我只穿了件单薄的睡衣。他的身体一点点向我靠近,最终把我揽住。我可以感觉到他毛衣的纹路,那是一件粗针织的暗绿色毛衣,洗得很旧了,长度上正合适,但宽度上是松垮的。他真的很高,即使我比大部分女生要高上一头,也还是在他身边显得十分娇小。
我感受到他的呼吸在加重,也留恋他给我身体带来的温度,但理智尚存。终于,我在他试图解开我睡衣的纽扣时制止了他。
感应也许是有,但还远不够深刻。况且我不敢相信他。青旅这种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年轻姑娘,而我又能有什么特别之处?他怕只是追求一场露水情缘,跟谁都一样,只要天时地利。比如今晚,女生宿舍里只有我一人。
我就此进行了一大段论证,但逻辑无比混乱,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。我没有让他再靠近我的身体,但也没有叫他离开。我想听他讲自己的故事。
“整个故事太长了,讲不完,就从一段说起吧。”他给我讲起作为酒吧老板的曾经。
大二那年,他拉投资,找合伙人,在家乡考纳斯的老城广场上开了一家酒吧。他的本意是搭建一个文化空间,所以举办音乐会和脱口秀,策划沙龙和戏剧节,通过五年的时间把酒吧做成了当地的文化地标。五年以后,房租合约到期,房东把店面卖了,酒吧也就停办了。买了店面的公司竟然要冒名继续营业。他去打了官司,打赢了。
“其实五年的时间也足够了,酒吧达成了使命,我也就去开始下一个任务了。”那段往事在他的讲述中显得珍贵又遥远。
不过后来,我真的在网上找到了那家酒吧,更不可思议的是一篇报道那场官司的新闻稿。酒吧的页面还在,上面留着几年前的评论和照片,依稀勾勒出往日的盛况。照片好像某部文艺电影的截图,里面的人全都打扮得别致,举着酒杯在彩色暖光下谈笑。Ignas也在照片里,除了新留的胡子,这些年好像没怎么变。
他今年三十三了,比我大八岁。在关停酒吧和现在之间还发生了什么,我没有来得及问。夜实在太深了,而我明天一早就要启程离开。
第二天我又很早醒来,好像做过一场梦,但又不记得内容。明明只睡了一小会儿,但又亢奋到无法感知困意。我把背包拿下楼,在客厅和过道里反复徘徊。我想走之前再见他一面,虽然我不愿意承认。
我们一起吃了早饭,他做的黄油煎蛋配我买来的草莓。我夸煎蛋好吃,他说草莓很甜。我们默契地没有提起昨天晚上的事,直到厨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人。
后来我又试图分析过那天晚上的场景。其实他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,在我拒绝后也是尊重的。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,他说下次再见。我分不清是真心还是假意。他还是穿着那件深绿色毛衣,弯下腰来和我拥抱告别。
有一瞬间我打算改变行程,只为和他多相处几天。他和我说过,要等上一个不忙又晴朗的日子,坐渡轮到一个无人荒岛上露营。我想留下来,叫他带我一起去。但我没有那样做,最终还如期离开了。离开前我悄悄把那支花投进海里,好像这样就可以做了结。可是那天的海很平静,一点浪都没有,花在海面上飘了很远,就是不肯沉下去。
任凭往后的旅程如何精彩,他的身影总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我又遇见了许多有趣的人,我总希望会有人让我忘记他,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。他对我的吸引力强大到近乎危险,是许多种感觉的结合体。我能感知到他过往经历过的生活,和被生活打磨出的松弛感,还有沉淀下来的疏离感。而相比之下,我单薄得像一张白纸。我知道,心动于我是无比珍贵的,我怕它转瞬即逝,要拼命抓住。在开始这趟旅行前,我刚刚结束一段短暂的恋情,对方是个温暖又坚定的人,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我策划了很多遍要讲的内容,可真的讲起来又全忘了。我靠在床的一侧,把手机放在另一侧,开着免提,尽力让声音显得平静。我向他诉说我的心境,给他描述我想要抓住的感觉。
我还是摸不透他的心思,我不确定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。但这也不重要,我知道我想要什么。我想逃离那盘棋局,去试探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,体验我从未经历过的诗意浪漫。结果会是什么,我不知道。或许是命运的转折点,或许是多年以后还会想起的故事,又或许只是漫长人生中一段无关紧要的小插曲。未来仿佛一面打碎的镜子,分出无数道棱,纷繁得扎眼。
把感觉具象成文字的过程,也是直面自己内心的过程。写作是一场自我探索,同时也是一次自我疗愈。感谢三明治让我记录下这一个故事的开头,希望还能回来补充后续。
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,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,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,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。